6月14日晚,纽约大学(NYU)比较文学系、东亚研究系教授,国际批评理论中心主任张旭东教授应邀来到苏州大学为唐文治书院学子开展了题为《“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鲁迅的“文体混合”与<伤逝>再解读》的精彩讲座。本次讲座由唐文治书院季进教授主持,王尧教授、书院青年教师以及书院全体同学一起参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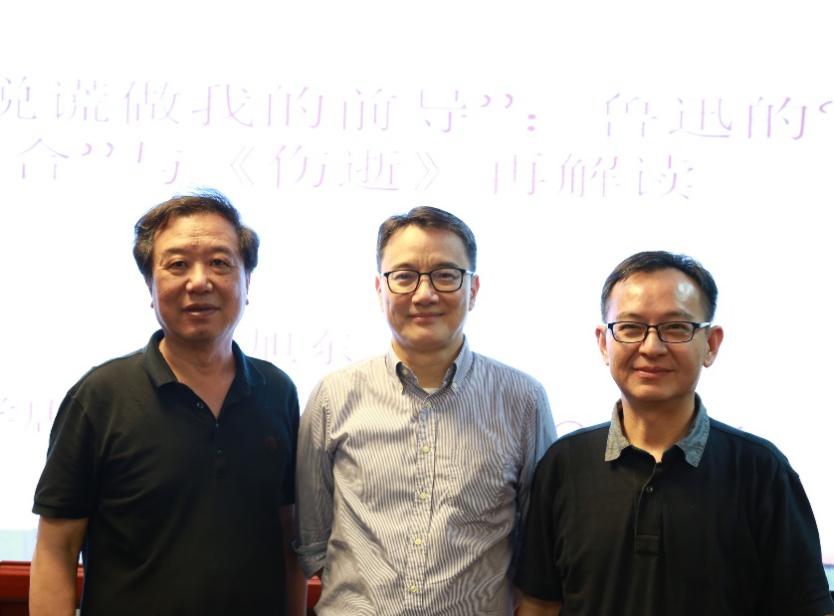
张旭东教授首先从“什么是‘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这个问题导入,提出小说的最后一句话“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实际上是一种伪忏悔、伪表白,这就使得整篇小说变得不明确了。带着疑问和悬念,张旭东教授对《伤逝》展开了深入的剖析。
《伤逝》在鲁迅“过渡期”或“杂文自觉”过程中处在怎样的位置?《伤逝》为《彷徨》系列倒数第三篇,其创作时间距带有“杂文的自觉”宣言性质的《华盖集·题记》只有两个多月。《彷徨》系列的第一篇作品《祝福》完成于1924年2月7日,为鲁迅“沉默的1923”之后的第一部作品,是“过渡期”及“第二次诞生”的象征性开端。很多读者对《伤逝》的解读不满足于“自由恋爱及其局限性”框架,却又苦于找不到其他打开文本的角度和方法。但若将之置于1925年秋鲁迅生活和写作状态的直接语境来看,这篇小说便可以显示出它与同时期鲁迅杂文的高度的母题关联性和语句层面上的互文性。而在自由恋爱和女性解放的问题上,《伤逝》则并未提供类似《娜拉走后怎样》的观念、思想、建议或“情节”。
在叙事上,《伤逝》体现出了叙事口吻、叙事结构乃至文学语言的暧昧性、游移和“虚假性”。其叙述语言和叙述口吻亦具有二重性。鲁迅在描写一个虚构人物时,若使用的是小说口吻,那么这个人物便多为自私、软弱、自恋的。《伤逝》这篇小说中鲁迅以小说口吻描写男主人公,以男主人公代表近代主体的“滑稽”:他对外界世界不满,但又无法改变外界,只能改变自己,生活在个人情绪化的小世界里。在小说语言之外,文中还间杂着杂文的话语,反映写作者以批判的、严厉的、悲剧的眼光审视着小说,在建立小说的同时也在不断瓦解着小说。

张旭东教授随后具体分析了《伤逝》的几个母题:情感教育、自我持存的政治、现代性主体内部分裂和自相矛盾的“分析性叙述”、“美丽心灵”剖析与“主体的滑稽”批判、“杂文为体、小说为用”,并以文本为例,展示鲁迅笔下的人物形象、动作、情节乃至内心意念的杂文化。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伤逝》题目中“伤”的是什么,“逝”的又是什么:不是向“爱”告别,而是向“不爱”告别;不是向“新的生活”告别,而是向“旧的生活”告别……这是将所有的一切都打包在遗忘和说谎里,然后继续往前走的行动,同时也符合五四“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发展情况,符合鲁迅写作向杂文转变的境况。这是鲁迅杂文写作从自觉到自由的转折点,借助小说残存的虚构艺术的暧昧性、审美的模棱两可性,为杂文真实的笔触铺路。
最后,回到“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中“遗忘”和“说谎”的问题,张旭东教授对男主人公涓生的话做出了阐释:他的行为和话语展现出了单纯的指向性、动机性以及作为其驱动力的虚无主义唯意志论,他的遗忘则是他面对造成子君的死亡的自我防护。
张旭东教授讲完之后,同学们就讲座内容踊跃提问,师生进行了精彩互动。至此,此次讲座圆满落幕。

通讯:徐天鸿、杨玉洁
图片:宣传部
审核:王磊 事务中心主席团

